剧情介绍
一家三口的生活因父亲伟明被查出末期肝癌而改变。表面上平静的家庭被阴霾笼罩。妈妈慕伶扛起家,却得不到父子的体谅。儿子一鸣收到美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但不敢告诉爸妈。他知道母亲不易,却不愿表现过多关心。父亲伟明则在迷雾之中暗自做出一个改变家庭命运的选择。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钢之炼金术师完结篇最后的炼成祈愿病历簿研修医的解谜诊察记录诈骗大师惊蛰全美超模大赛第十七季虾球传巨鲨大战食人鳄杰茜驾到第四季无声的抵抗盲盒旅行局你不要走1978意大利版江湖医生少年体校粤语女黑手党失落的海峡啊朋友,再见!探案拍档第四季成年人不懂如何恋爱嘿,老头!服装店的故事帕索里尼向幸福前进永恒的初恋急往迟返黑色喜剧 黑色喜劇血胎换骨阿亚潘和柯西(英语版)信长协奏曲电影版我们的岁月镜花水月第四季
长篇影评
1 ) 让喧哗通往低语
《小伟》有意地模糊虚实界限,却不是通过暴露画框的设计完成,相反地,它改造画框内的可用元素(包括声音),让观众在解谜游戏的参与中与创作者一同完成对影像感的构建。
有一组合段实有此乐趣——由一鸣和朋友逃课开始,到他回家路上责问丽娜是否因她告状致使朋友被惩罚结束;朋友陈晋南的回力鞋和马刺球衣成为被移置的元素,当一鸣在教室回过神来时,我们看到他穿着一件马刺logo的文化衫,而除此和结尾最后一幕之外的其他时刻他始终穿着印有"BERKELEY"的衣服,如果BERKELEY代指他对加大、美国的向往,在这一幕里马刺logo则是他怀念以至将自己代入离去朋友的象征,且导演还要借老师和同学强调他只有一脚着鞋;还有回家路上那只挂在书包上的回力鞋,回到房间也要把它摆在书桌上,在拍到房间里的一鸣和远端的母亲这一画面中,鞋子处在画面中心,且受到画面中唯一光源——台灯的照射,递进强调的过程亦象征生成的过程。那么突如其来的呕吐和白日梦中动作的回流作为过程外的、例外而荒诞的瞬间,正是对这种后悔、难舍和「为什么自己也参与了却无须担责」的不解下所生成的错位感最具概括意味的人物反应,与象征符号的渐强形成张力。
另一段超现实情节也有类似的移置操作,出现在伟明的梦境中,哥哥带伟明去看祖坟时,镜头先是对着伟明,而后随伟明视线向前望去,变成了「此前给他们一家三口搭顺风车的司机」牵着「虚实间的伟明在泡沫厂遇到的小孩」在前方领路,镜头再往回摇,哥哥在中间,伟明依旧在后。这是一组对位关系——在伟明的梦境中,日间遇到的司机和小孩被当作哥哥和他的儿时虚像。还有伟国说这是爸妈的墓,然后伟明将梭子叉在父母墓前札起的渔网上,这个梭子是前面幻景中母亲给的,这些象征构成了伟明潜意识中对少年时家庭光景的怀念,堪比《野草莓》结尾中同样行将就木的老者看见年轻的父母和自己在湖边钓鱼时面露微笑的情境。

影像感不只是靠前述般符号的移置替换完成,还需要什么?游戏性也不能显而易见地冲击或者替代影片的表意,如何掌控它?对景别的选择就成为处理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回力鞋处在明亮的中近景的画面中心是一处范例;再往前倒,近景中一鸣和朋友在走廊聊天,一鸣被告知「保安据说仍在昏迷」,而后他转过身去,切到中景时浅焦镜头对焦在一鸣的背,随其视线缓慢聚焦到远景,远端的朋友被带走,带出的信息是他受到处罚,也就确定前者的「据说」为事实,同时一鸣与惩罚事件保持着一段距离……
在这一段简练准确的镜头组合后,随即切到下一场景——被选作海报的深焦大全景墨绿雨林里,角色作为一个点移步入画,当我们在后面知其为超现实画面时,巨大落差的切换才不至突兀,反倒从远处看时人的朦胧感是契合该语境的。
结合影片的其他桥段,例如中近景时幕伶两次面对镜面抹泪,以及一次是扶着伟明进家门,另外两次的镜头运动是由幕伶要阻止一鸣问出真相、伟明吐血这样的被动情节中从镜面中快摇到现实;再例如两次隔壁家老奶奶的出走,第一次镜头从墙壁的特写到片警把老奶奶带回家到缓慢摇至站在楼下远看这一幕的幕伶,第二次镜头静置在一鸣取下并浏览录取信、喜形于色地跑上楼梯后十几秒,我们见证了老奶奶再次出走,两幕都不算长,但景别和情节都似自然流淌变幻而过般不泛涟漪;再如那段颇有一番设计的医院长镜头……
我们或许可以概括出一些景别的运用规律了——近景展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以及在它之下单个人物的情绪、心理。中近景和中景在这个基础上纳入了城市空间,一方面它向我们展示人们的连接和情绪与空间存在的微妙关联,抑或它是怎么制造人之隔阂的,而不解释为什么;另一方面也在画框内留出空白给人物的外显表达,而非如近景聚焦其更细微的心理和情绪。全景、大全景则不再以人为主体,物理空间占据了巨大的比例,可却并没有被压缩成平面景观,它似乎蕴含某种同样巨大的自然,将影片发生的一切吸纳其中,突然想到《春江水暖》,我会认为这也是它想做可显然完成度不及《小伟》的。
更系统性的镜头语言十分难得,毕竟凭自己的喜好滥用某一类语法造成空洞风格化问题的处女作不少,《小伟》不在此序列内。但系统的、工整的同样可能发展为风格的、空洞的,为此作者给出了一个很巧妙的解决方案:以丰富明显的声音设计替代配乐,在医院长镜头一场戏中镜头运动由隔壁病房紧急求助的声音开始,随护士推车声和脚步声快速跟进,在幕伶折返时虽然画面仅容纳了她的脸,但背景里不同病房传出的抽水声、机器声、讨论声穿梭而过,就像战争片里在营造士兵穿梭过战场的感觉时那种处理方法,而回到病房伟明即将出院,也就是说它在同一个镜头内部就完成了时空转换,她竟是穿过了一个时空战场——显然,日常且丰富的声音加入填充了时空感,使得同一镜头内部的情景转换变得平顺甚至不易察觉。
通过有声源声音扩展画面外空间是较为常见的手法,可不必自始至终地使用也能保持生活感之连续,也可连接时空重新定义眼前的景观,却是《小伟》载着伟明回家的街道充满喧哗,一鸣回忆里的密林被赋予了神秘低语,氤氲缭绕的废旧泡沫厂传来熟悉而遥远的敲打声——日常的、离散的喧哗最终通往在永恒时间中低语的自然,体现出「阿基里斯与龟」式的连续性,永远存在的极限也就不再值得计量,追寻生活真实的答案需要的仅是一个方向,而不是答案。

回到影片整体上,纵观带有自传性质的影片,虚实交错的叙事方式,相比暴露画框或者更高层级的叙事者,如《阳灿》中在老莫一场戏中姜文的画外音,或是《痛苦与荣耀》结尾阿莫多瓦在画框外的现身,其个人回忆部分以及它带来的叙事不可靠性自然是更隐秘的,故事也就不再依附于叙事者的回忆,而具备了某种原发动力,一方面它将导向更温声细语的影像气质,可另一方面,导演的自传回忆冲动又如何与故事的自发冲动调和?不,这个问题在他选择这种叙事方式时已然模糊了。当虚实交错的梦境替代和修补现实关系时,我们就很难分清这两种冲动到底是哪一种获得了发展,哪一种被抑制。我可以理解回忆被选择以这种叙事方式转化为影像,可当做出这样的选择时,作品的充沛情感及美学价值就被置于首要位置了,而与自我、与回忆对话之意义则要次之。
2 ) 命脉相连!这样的处女作着实令人惊艳
看死君: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没几天,但已经很少有谁提起那份获奖名单了,更多的是被文章马伊琍离婚、海清的“女演员宣言”等获奖影片之外的新闻所淹没;以及这两天被更为广泛讨论的“暂停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又不得不让人想到这几年同样力捧青年导演的金马奖的举步维艰。

近十年来,中国电影似乎从没有像今年一样被集体唱衰过;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有好电影诞生。当真正的好电影出现时,我相信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更何况,在这青年导演队伍日益壮大的当下,每年从FIRST等影展向电影市场输送的年轻血液中,也都不乏年度黑马之作。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部电影,便是荣获了本届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大奖的作品,黄梓导演的《慕伶,一鸣,伟明》。作为今年影展的四部惊人首作之一,本片在众多参赛片中显得有些特别,它看似只是一部司空见惯的家庭电影,却在其中埋藏着太多的“宝藏”,拥有非常大的解读空间。

命脉相连的一家三口的日常琐事,面对沉甸甸的生死命题的半梦半醒,以及逃离现实和回归自我的相互拉扯。关于家庭,关于成长,关于青春,关于告别,影片《慕伶,一鸣,伟明》就像是一支悲喜交织的奏鸣曲,暗涌出独特的生命体验。

正如片名所呈现的那样,影片以三段式结构讲述一家三口各自不同的人生,并最终拧成一个绳结。看似是彼此分割的不同视角,追根溯源之下,却都殊途同归。那条缠绕在母亲、儿子与父亲之间的隐形纽带,赋予了这个生命共同体既温柔又悲伤的因子。或许,这也是很多家庭的共同宿命。

影片第一章节以母亲幕伶的视角展开。跟随着手持镜头,慕伶只身去学校寻找儿子,貌合神离的母子关系仅寥寥片语便凸显出来。而在得知丈夫已身患肝癌晚期时,她的内心更是承受着如排山倒海般的痛苦。作为家庭主妇,她不得不维持平静的假象,而不让丈夫和孩子知道这一真相。

处于叛逆期的儿子一鸣,把学校当作一个巨大的失乐园。与同学偷偷躲在厕所吸烟,上课期间爬墙逃学,还有对母亲的疏远隔阂。身处青春期的他,总是冒险又不甘。他一边对出国留学充满着向往,一边却不忍心抛下病重的父亲。复杂的家庭情感时不时地将他拉扯进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乌托邦梦境。似乎唯有在那里,他才没有这样的烦恼。

第三章节中,父亲伟明的视角更耐人寻味。虽然是触及死亡这样一个让人避而远之的话题,但这个故事中,导演以超现实角度将死亡化为一种绵软的生命形式。梦境与现实彼此交错,灵魂和肉身相互叠加。伟明的意识脱离于肉体,回到了故土,见到了已故的老母亲。而幕伶、一鸣和伟明在最后的无人村落和回家的火车上,达成了情感上的共鸣。之前所有的埋怨、不解与厌烦,都随着那一趟回乡之旅悄然化解。

专访《幕伶,一鸣,伟明》导演黄梓
采访 | 看死君
看死君:导演好,这部电影的片名是一开始就定好的吗?
黄梓:对,这个片名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了,甚至可以说是先有这个片名,才会有接下来的故事创作。电影分了三个人名、三个段落,每个段落都以其中一个人作为主观视角展开故事,片名就是一家三口,里面三个人的名字慕伶、一鸣、伟明,分别对应的就是妈妈、儿子、爸爸。

看死君:我发现电影的英文名叫《All About ING》,关于ING,除了对应三位主角名字的拼音后缀,还有什么用意?
黄梓:是的,ING其实就是取谐音,就是ING,同时ING在英文里面有现在进行时的意思,我想表达一种当下的感觉。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没有离开现在当下的感觉。当你回忆过往的时候,其实历历在目的感觉也是一种当下的感觉。

看死君:这三个人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黄梓:其实是取决于“伟明”这个名字,因为我爸爸的名字里面就有“伟”这个字,而我爸爸姐妹的名字里都有“明”这个字,所以我就把这两个字组合成了“伟明”,其实就是我当下的一个偏好。至于“一鸣”这个名字,我一直都挺喜欢的,我喜欢“一”这个字。而“慕伶”是因为我也很喜欢“慕”这个字。
看死君:作为长片处女作,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黄梓:其实影片的故事多多少少有我个人的印迹,是根据我的成长经历和生命体验去编写的一个故事。虽然很多剧情其实是编的,但是里面的人物原形其实就是我和我家人。

看死君:所以,您自身的经历投射在影片中的占比还挺重的。
黄梓:是的,我爸爸确实生病了,我也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其实我爸爸生病是在前几年,那时候我刚刚留学回来,待在家里耗了一两年没啥事干,忽然间我爸就被查出病情。我当时的心里感受就是特别想离开,因为太压抑了,每天发生的种种,让我不知道爸爸的病情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走向,所以我就有一种想逃离的感觉。包括我高中时期的状态,我跟父母的关系,我当时也是非常渴望逃离,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城市,去到很远的地方。

看死君:所以一鸣这个角色,也是您个人的缩影。
黄梓:是,其实我就是把生命中两个比较困惑的阶段,交叉融合到了一起,变成了现在电影里面一鸣准备要出国,但同时他又遇到了爸爸生病的情况,面临着亲情的羁绊。他到底是选择出国,还是留在家里。

看死君:影片开头通过电视屏幕出“慕伶,一鸣,伟明”这个片名的方式很巧妙,可以谈谈这个构想吗?
黄梓:其实我想做成一家人在一个休闲的下午,母亲给父亲染头发,儿子本来看着电视,看着看着睡着了,躺在沙发上;他们没有哪个人是在认真看电视。出现的一些镜头其实并没有很清晰地带出这三个人的样子,包括母亲给父亲染头发,我都没有给他们一个正脸。而他们的真正容貌展现其实是在电视屏幕里面,他们开着摩托车,但整体还是模糊的。
看死君:影片中有三个章节,前面两章都是按慕伶和一鸣的视角来叙事;但第三章却没有完全按伟明视角,为什么?
黄梓:我觉得他们整个家庭关系的走向,虽然三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状态,但他们需要面对的都是爸爸生病的事情,而他们可能有各自面对的一个方式,他们也没有去跟另外两方一起建立起一个怎么样的沟通,达成一个和解。从一开始他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还是偏独立的,或者说他们的关系本来便有一点疏离。

所以到了爸爸段落,虽然一开始也是他独自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慢慢地到后面,尤其是他们离开了广州,到了爸爸以前出生、成长的地方,我觉得他们是有在情感上面找到一些联结点,所以那个视角并没有特别地只是专注于其中一个人。
看死君:为何会在第三章节加入梦境与现实相结合的场景?
黄梓:这个处理方式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戏剧冲突特别强的东西,我不想只通过他们面对客观困境的方式去表现他们的家庭关系,也不想简单地以事件或者剧情来塑造他们的关系以及角色。我想在最后这部分,通过建构空间的关系,加入一些虚无的情感的连接。

父子之间的情感最终在岛上联系在了一起,虽然他们并没有进行太多的有效对话。他们分别进入无人村,见到了以前的老房子,但是他们看到的房子是不一样的。爸爸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对回忆的一个重现。弥留之际,他开始有一些意识的投射,让他看到了一些与现实中不一样的东西,包括老房子里面还住着他的老母亲和他的哥哥。那是他的一种意念的传递。
儿子一开始进入无人村其实是最写实的,然后我用了一个平行剪辑的手法。其实那个老房子跟无人村里的其他房子一样,已经多年无人居住了,会让我们意识到爸爸看到的其实是他的某种想象。但是当儿子追寻着缝纫机的声音进入到一个老房子之后,里面又有一个中年女人,她在用缝纫机做衣服。

她的穿着打扮是一个当地农村妇女的样子,还跟他说了一些他听不懂的方言。但是,那些对话其实是他带着爸爸的意识,在跟母亲进行对话;也就重现了他爸爸和他奶奶当年的对话。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时空融合到了一起,由于儿子在当下也遇到选择出国还是留下的问题。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有点像爸爸当年跟奶奶的一个关系。

看死君:影片的剪辑非常出彩,尤其是超现实部分,能否谈谈剪辑方面的构想?
黄梓:确实我们这部分花了很多时间,想着怎么把它剪好,担心在虚实处理的环节上很容易让人觉得有割裂感或者是有点太刻意。现在影片中的最终呈现是我跟剪辑师都觉得比较满意的结果了。因为我们又去补拍了很多,这其中有很多层次的叠加,原有的素材确实没办法支撑起我们想要的那种状态。

看死君:影片结尾处,幕伶和一鸣在收拾伟明的遗物,然后手持的镜头晃动着离开,这是以父亲伟明的视角吗?
黄梓:我自己也是这么理解,但是可能有些人有别的解读,我当时创作的想法就是想要有一个父亲的视角去做一次告别。可以理解成父亲以一个灵魂的形式存在,他的意识还存在于这屋子里面,但是母子并不知道。她们把父亲的衣服收拾好然后丢掉,是一个要继续生活的态度,父亲看到这一切后,就慢慢地离开了这个家,作为一种告别的方式。

看死君:再说一下最后这个镜头吧,从渐渐过爆到变成一个全白的画面,为何这么处理?
黄梓:这场戏其实是在现场临时想到的。他是一个主观的视角,他看到的世界就会有一个转换,因为他可能要离开,离开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可能去到另外一个维度的感觉。所以我想用曝光的手法,类似父亲的视角去表达不一样的细节。

作者| 想成为猫;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采访| 看死君;转载请注明出处

3 ) 《小伟》:一个中国家庭的爱与疏离
《小伟》是青年导演黄梓的处女作,导演本人看上去青涩、内敛,声音也软软的,带有浓浓的南方口音,是个不怎么张扬但内心坚定的人。拍《小伟》的时候,黄梓还不到30岁,但故事已经酝酿了三四年,期间他四处找投资、跑创投,想要将这个带有自己私人情感的家庭故事拍出来。
而这一切都始于家中的一次重大变故,即在他从纽约大学艺术学院退学回到广州,又没有正式工作的时候,黄梓的父亲突然得了癌症,并于不久后离世了。
电影是导演的回忆,也是一个梦,大概逝去的亲人,只能在梦里相见了。
《小伟》的故事三个段落组成,每个段落对应一个人物视角,分别是母亲慕伶、儿子一鸣和父亲伟明,主要讲的是父亲伟明确诊肝癌晚期之后,一家人生活上的改变和他们各自的困境。片中描绘的家庭生活也是导演本人家庭生活的缩影,一家人既紧密相连,又各怀心事,而在这家人的爱与疏离中,我看到了一个中国家庭的真实面貌。
电影中,父亲患癌之后,种种问题扑面而来,首要的问题便是家人是否要告知伟明他的真实病情。母亲一开始选择了隐瞒,联合儿子、亲戚朋友和医生护士们共同制造了一场骗局,告诉伟明他只是肝硬化,让他放宽心,于是在这段时间里,除了伟明本人真的感觉轻松,身边的人都只好故作轻松、强颜欢笑。然而想瞒不见得瞒得住,随着病情加重,病人的怀疑也就越深。就在伟明开开心心回家的当天,他吐了血,那一刻他全懂了。
作为一个成年人,理论上,伟明对于自己的病情是有知情权的。但在实际生活里,大多数家庭担心患者承受不住,纷纷选择了隐瞒真相,能瞒多久是多久,甚至有的癌症患者直到去世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家庭是一个联系紧密的集体,更缺少个体的权利意识,家人们会很自然地觉得我有责任替病人做主、替他承担这份精神压力。
问题是,这样的事真的可以被家人替代吗?
中国的家庭看上去联系紧密,什么事都要一起面对,以为这就是爱,却缺少对彼此个人边界的尊重和有效的沟通。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家庭题材的电影关注到这一点,如在去年金马奖的最佳影片《阳光普照》中,父亲都可以为了儿子好去杀人,却不能关心和理解一下自己的儿子真正需要什么。
同样在《小伟》中,活在一个屋檐下,三人之间也有着或多或少的疏离感,病情暴露之后,父亲在家中养病,感到失落,开始自暴自弃,儿子在学校抽烟、翻墙、翘课,母亲则忙里忙外的,是最辛苦的一个。
然而从父子二人的视角看过去,母亲的辛苦并没有被看到和理解多少。电影中有一幕是一鸣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母亲在门外冲他喊:“隔壁的婆婆走丢一周了,我不明白她家人为什么不去找她,你是不是希望我像她那样你就开心了?”这一刻,母亲因家人长久忽视自己而积压的不满终于爆发。
这里也反应出中国家庭内部存在的另一个普遍问题,即女性在家里不受重视,女性在家中的劳动付出也不被看到。
导演本人也说过,他觉得中国社会的家庭,女性不是在一个主导的位置,所以电影中的母亲更多成为了父子的陪衬。
现实生活中,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常常是被忽视的,虽然我们的社会文化惯于把照顾家庭的责任归到女性身上,但是家庭中的劳动,既不像社会上的工作可以换取实际的报酬和社会地位,还可能被家人们视作理所应当,认为女人们天然愿意为爱付出。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就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犀利指出:“所谓的女性专有领域的‘关怀’、‘照料’实际上是‘以爱之名的劳动’( a labor of love)。无论用何种意识形态来粉饰遮掩,女性在家中所进行的工作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并且是如果她们不做的话就必须找人来代做的‘劳动’。而家庭主妇们只能在‘爱’的名义下默默承受。”就像上野千鹤子说的,家庭中的劳动是有价值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却总被社会文化认定为这是女性的责任而非男性的,可即便有家人们的肯定和感激,也不能说这就该是女性做的事。
就在不久前,华坪女高张桂梅校长怒斥她的一个女学生做了全职太太。不自立自强的视频流露出来,又掀起了一波关于女性做家庭主妇就不是独立女性的论战。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并不认可家庭主妇的价值。但与此同时,仍然还在要求女性要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事实上,许多女性就是在被社会文化要求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的前提下,才处于无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困境之中,被迫中断职业生涯、回归家庭。
而在家庭的这种疏离背后,还有深沉的爱。电影里,慕伶、一鸣、伟明三人之间细腻、复杂的情感是非常动人的,就像伟明一时崩溃,把药扔到地上,慕伶也生气不理时,一鸣会默默地将地上的药一颗颗捡起来、放回去,他们三人始终彼此关心,即使不爱言语。
电影结尾,伟明离世后,母子俩一起平静地收拾遗物,怀着共同的哀伤,生活继续,突然移动的镜头仿佛是父亲的眼睛,仍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家。
绝症和死亡带来的哀伤,逐渐填满了这个家庭的裂缝。
而在电影之外,通过感受这个家庭的变化与处境,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理解自己的家庭以及我们的社会文化。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被看到、被理解、也被爱着。
——首发毒药,勿转——
4 ) 无法被察觉的变化,“宜家”,以及和解
之前有一段时间很讨厌家庭题材的故事,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原因,一方面是看了很多并无法做到“客观”去描述的家庭故事。《小伟》的三段性叙事,其实很大程度上助益了“客观”而又“主观”地去阐述一家三口中的每一位,在自己的故事中,其实其他人都会相对地没自己那么好,但三个视角看下来,在真实性最大化的情况下,还是能够通过三个人主观而又令人稍微抽离的视角去对这个故事感同身受。
也在公映之前看过一遍,成都叢林办的“夏日重逢”企划,当时还对那几个难以调度的长镜头、超现实镜头,还有一看就知道勘得很仔细的景有更多的技术方面的思考,而这次公映与背景近似的两广朋友再看,反而也抛开了对“完成度”(为什么是处女作却完成得这么好)的疑问,而去感受这个故事本身。 也可能也是因为在这半年间,生活与世界还是变幻莫测,这次观影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可能在家庭题材之外,最后这个故事所要和解的并非是“家庭关系”,而只是那些并无法在“主观”下察觉到的变化本身。就好像“伟明”与“尾声”衔接的那一场戏,动车匆匆而过,而生活还是会继续。
以前在广州的时候很喜欢去逛天河北的宜家,在没有动力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在宜家里看到的家具、摆设,总能让我有种错觉,是在未来的某一刻,也能过上那种如同样板间的幸福生活。刚好这部电影的英文名也叫“ING”,“宜家”和“ING”,白话烂Gag的恰好重合。 但其实《小伟》又不是那种幸福的样板间,每一句台词都能在所想要逃离的传统家庭环境下找到近似样本,这种如同被洞悉了过往20多年的人生的冷静视角,反而也能让人找到一种把这种生活当成幸福样板间的心态。
其实人还是有贪欲的,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因为无法脱离社会而害怕成为走失的痴呆老年人,才会对自己早已心知肚明的问题产生不理性的疑问,才会在某一次阳光晒下来的时候怀念故乡的阴冷。 但本身在生活之中,每一个词语又都不会是单纯的“褒义词”或者单纯的“贬义词”。贪欲反而也会变成一种现实地去爱别人的力量。 虽然嘴上说的是“我地咁高你点解会咁矮”、“我似你咁大嘅时候都出来广州打工啦”、“唔好逼上来啦床咁细”,相互折磨是因为相互疼爱,因为可憎所以也可爱。 可能广东人的乐观心态也是这样来的吧,“幸好我什么都不是”,所以“幸好我什么都可以是”。
所以即使并没有一字一句在互相阐述着彼此对自己的重要性,而也的确“主观”视角里的自由、束缚和回忆是并无法让其他人真正完全感同身受的,最后的结局,还是在用一种生活态的形式,纪念着每一个对自己重要的人。 这样也算是真正和解了吧。
5 ) 广州记忆的着陆与离地
删减稿载于微信公众号“识广”,作者均为本人。
1
上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广州故事是什么时候?
银幕上的广州故事,必然不能避过不提《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拍的是冼村拆迁背景下的都市爱恨与仇杀,广州沦为背景板,与故事的奇诡异色嵌合相衬。其余的,最接近广州的影像故事,无非是香港电影——与广州相似程度达不到十成十,不过至少说着粤语,因着香港文化在上世纪与千禧年盛行,某程度上也共享着文化背景。但更贴地的——譬如我们每日做广播体操的中学生活,要兜多几个圈的老式居民楼楼梯,家门口的半截露台,堆积着封尘的《南方都市报》……却无从寻觅。
无怪乎我们看《路边野餐》的乡野摩托之旅,有一种奇异的熟悉——明明贵州是异乡;在《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记忆爱淋雨爱说垃圾话的青春期;在《志明与春娇》里对粤语机锋会心一笑;甚至在更远的山西,小武穿着喇叭裤在街头闲逛,也不免怀想:我们也有过这样的闲散日子,或许是在上一辈。
我们早已习惯在其它城市的影像里拼凑和想象自己的广州记忆。而2019年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大奖的电影《小伟》里刻画了最真实的广州记忆。
电影原名《慕伶,一鸣,伟明》,片名分别是母亲、儿子、父亲的名字。电影由三部分组成,以三个家庭成员的视角讲述父亲罹患癌症之后一家三口的家庭生活:父亲患病后,母亲慕伶坚韧地撑起整个家庭,为了向丈夫隐瞒病情,请求医院的护士把病情诊断上的“肝癌”改成“肝硬化”;儿子一鸣为了陪伴父亲,原本打算高中毕业后出国,如今犹豫不定,时常在校园和街道之间迷茫地游走;父亲伟明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回到了家乡,迷雾之中,过去的记忆忽而重回心头……
影片伊始,坐着一家三口的轿车里,父亲伟明讲起病人因医院诊断错误而死亡的笑话,与负责开车接送出院的亲戚一来一回地闲聊,就足够勾起广州人关于家庭日常对话的记忆。
影片第二段儿子一鸣的视角里,有更多独属于广州人的中学回忆。为了逃避学校的广播体操,学生们跑到厕所里抽烟吹水;坏孩子们帮衬学校小卖部,偶遇“仇家”起争执,后来化敌为友又一同逃课到学校后山嬉戏。“劈雷”“劈撚”等本地广州人都不记得的粤语脏话不时出现。
为了散去烟味,一鸣从天桥跑下马路,穿过桥底,跑过省皮红绿灯、地铁下的高架桥。汽车鸣笛声,放学后孩子在街边嬉笑,下班的市民拿着大袋食材走过……广州二中、76中、恒福路、华乐路快速掠过,广州街景街声熟悉可感。
2
“这是一个可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故事”,导演黄梓在广州提前放映场的映后谈里说。如何面对死亡自是一个普世故事,东方式含蓄的亲子关系更是中国最普遍的命题。只不过因为他是广州人,大部分的人生在广州度过,这部具有半自传性质的影片自然有着广州印记。
一个关于死亡的家庭故事落地在广州,在导演黄梓的处理下,摆脱了煽情的流俗。无法言明、未曾留意的情感以笑话、顾左而言他的形式呈现。譬如母亲慕伶在医院装作责骂护士写错病情诊断让丈夫宽心,一边又双手合十向护士表示感激。对应地,伟明说起病人因医院诊断错误而死亡的笑话,夹带着愤懑表示已然洞悉妻子的隐瞒。慕伶与伟明之间对于病情的心照不宣在影片中暗涌。又如儿子一鸣在天台朗读录取通知书,对父亲说不想去留学。甚而父亲的死亡最终都经由移动的镜头,从曝光过度的天台摇摇晃晃地去到有阳光照射的客厅,逗留在房间的走廊,变为一鸣说出的:“阿爸这件夹克,我都几啱身。”镜头最终选择停在卧室门口,与这对母子留下一段距离。
直白的“爱”在影片中缺席,却一遍遍地通过无字暗语说出。在明媚的广州影像中,因死亡而起的家庭动荡被拆解成一个个私人记忆片段,在悲怮过后摊放在阳光底下被逐件分拣、浸泡、湹清——一个可供观众进入的入口出现。记忆在导演黄梓的处理下,露出超现实的切口。
我们于是在这熟悉而陌生的镜头下重新审视这座城市以及其中的亲子关系。在影片的开头与结尾,父子在家中染发,母子在房间里收拾衣服,客厅都播放着一家人出游的录像。黄梓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应这种现实与录像并齐的处理:“我想要他们看自己,但好像又不是在看自己那种感觉。”一家人与录像中的“一家人”对视,我们也带着广州的生活经验、记忆与广州对视。
在这种目光之下,摩星岭呈现出奇异的广阔,与挤迫的城市相反。一鸣在找寻掉下山的鞋子的时候,往一片苍绿中扔了一颗石子,却忽然回到讲述阿基里斯追龟的数学课上,对于鞋子的找寻凝结于一个数学桲论:“阿基里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诗意从暧昧的影像叙事中离地而生。甚而,这种对视会发现熟悉事物中的陌生感、恐怖感。母亲慕伶像每一个中年女性,她带着哭腔骂躲在房间里一鸣——原来都曾坚韧地承担重负,偶尔柔情,时时被磨损得暴跳如雷。她的脸与你我的妈妈重合,却又未曾在银幕上看过妈妈的脸,总有种白日下的恐怖。
3
对于这位广州土生土长的青年导演来说,影像中的地域印记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地域与生命经验粘连,难以切割。黄梓接受识广采访时表示:“因为我在广州长大,之后即使去了别的地方,拍摄其它城市的故事,还是会带着广州的影子。”
对待这些生命经验,黄梓在忠实地沉浸与抽离地审视之间找寻平衡——自然,我们作为观众,在电影之中找寻的并非只是广州影像的忠诚再现。影片中超现实的部分,黄梓自述有受到毕赣和侯孝贤的影响。到美国留学再回到广州的经历也赋予黄梓观察故乡的另一种视角。
在自述《黄梓:未经审视的故乡是不值得拍的》之中,他认为创作者未经审视地面对故乡时,只觉得故乡无趣,然后陷入失语的状态,因此“离开故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代表着你会遇见更多未知。这种离开并不是说旅游两三天,而是说在别处构建一个完整且崭新的生活体系。……更重要的是,离开故乡能赋予我们一种超越感和距离感。当我们脱离日常的惯性之后,更多抽象事物随之袭来,它会逼迫我们去重新审视生活。”
这种审视的目光使得黄梓发现广州的有趣之处:“巷子深处,还有从网吧出来的青年,背着超重书包的小学生,把环卫车停到公厕门口,准备上厕所的环卫工人……‘轰轰轰……’有别于车辆经过传到桥下的回响,透过因高架桥拐弯而无法被完全遮挡的天空一角,我看到了缓缓飞过的飞机。”
着陆与抽离由此而生,这也是电影《小伟》区别于其它以广州为背景的影视作品最大不同之处。
然而这部广州电影却并未接触过广州的影视团队,所有拍摄资金均由导演的亲人资助。对于影片主角全员采用香港演员的举措,黄梓有过多次解释:在广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因为广东电视里平时放的都是很市井气的情景剧、长寿剧,那样的演员不符合我的感觉。”至于这部广州电影,似乎演员、资金、发行等各个方面,仅有市井情景剧的广州对于一个拍摄文艺片的青年导演都并不友好。
而在今年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广州导演蔡杰的一部讲述广州人到香港寻父的独立电影《人海同游》获得三亚关注大奖。2021年1月15日,《小伟》将于全国公映。
审视广州的另一种目光——那架在高架桥以外缓缓飞过的飞机,在等待被看见。
6 ) 清醒的私人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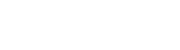




















竟然听到了熟悉的乡音,荒岛上冬天的海风真的瘆人,但岛上这段的确是全片华彩,拍出了苍凉落魄的美感。导演本人还挺可爱的。|SIFF2020第12场
3.5;首尾以及医院中游离拍摄对象的运动长镜相当惊艳,摄影机仿佛具有了某种(被赋予的)自主意识,仿佛幽灵的游弋;超现实段落与整体略违和,但我还挺喜欢的。独特的地缘风貌(地形、植被、水流、天气景观)与方言乡语,为影片搭建了一个内敛克制的情感系统,它勾连三代人的出走与回归,关乎的是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家庭如何处理生死问题,呈现出真实生活的肌理。细节把控十分到位,应该能激起亲历者的共鸣,那些无法出口的苍白安抚,自弃扔掉的药,强忍的打趣,直至最终结局的来临。一切都不可逃避,不会改写的结果,而生者仍要面对,仍要努力活下去,也会笑着谈起那个离开的人。处女作毛病都有,素材过芜杂,段落不平衡且略松散,不过未来可期。
你要做保安,他要做教导主任,我要开小卖部;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一上来就绝症,没有试图说教,也不用配乐去煽情,能把生死之类的大词,变成化整为零(ING)的进行时故事——作为处子作电影,已难能可贵。人生温度遽降的广州,似乎没有了全年的躁动暑气,医院、学校和家的不断转移,“似乎不为什么”的老奶奶离家、主人公逃课、年轻人出国,都在寻求解(救)脱(逃)。不足之处,是第三段似梦又遇,太“路边野餐”,感觉在试图去总结和升华。然而,真按照前两部分的节奏行进,也完全没有问题啊。主要角色均由港人演员出任,也是相当少见的、完全粤语为主的local电影了。
相当成熟的处女作,也是典型的半自传作者电影,看得出黄梓导演拍出了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三段式既代表三个不同家庭成员的主视角与三种有所变化的风格(由写实到超现实,从手持晃镜到稳定平滑),又呈递出了成长/新生与还乡/逝去的交织历程。基调冷峻克制,哀而不伤,在剪辑、转场(包括三段之间的衔接)、空间调度(自然环境&氛围营造,以及室内与画外空间运用)与视角过渡切换上也很有想法,尤其是主客观视点或不同视点的流畅转换,首尾相衔的幽魂视角运镜及通过电视中录像引入片名或收束全片的设计也十分惊艳。内容上留白和需要观者揣摩解析的地方也不少,对叛逆与压抑的青春及患病者心理的描摹很真实。第三段迷雾缭绕的无人村与停电后的荒凉宾馆足以将我吸入片中。美中不足的是仍有一些符号堆砌问题,如阿基里斯与龟和追日者寓言。(8.3/10)
愿意到电影院去看但是夸不太出来也不愿意说刻薄话的程度。
看完也很想点根烟。ps才发现广州的景挺适合拍电影的hhh
本届FIRST影展剧情长片最佳。拍着胸脯说是近三年来最好的华语处女作,时空性的完备程度秒杀所有阿彼察邦的拙劣效仿者。每场戏都有充足的信息量和解读空间,创作者有极其清晰的设计和考量,绝没有卖弄符号的心虚,剧作、表演和电影思维三者同时在场。一个在创作生态里越发“寻常”的家庭事件,用三人接力式的视角挖掘出每个成员的精神困境:死亡,青春,乡愁。联想和共情激起的思绪上下翻飞,无法止息。所有长镜头都没有露怯,有着丰富的细节和精准的调度。更不用说令人咋舌的景深镜头,对当下拍摄场景、人物内心乃至城市地貌都有深刻的认识。结尾与开头打通的幽灵视角直接把我看呆了,河濑直美《沙罗双树》的感动再次汹涌而来。自然、流动,让我耳目一新。
谁是追逐太阳的猎日之人,谁是与龟赛跑的阿基里斯,谁是笑话里拿错了病历的家伙,谁是现实中插错了卡的笨蛋。爸我想改变世界,这样的豪言在泡面的热度里融化。老婆快过来一起挤,这样的蜜语在卧铺的床位里蒸发。植入父亲离岛的记忆,在缝纫机边试穿祖母剪裁的黄衬衣,从此去天南海北,都带着你的身形。
虽然期望过高,但发现故事居然发生在广州,很是惊喜。一家人介于折磨与亲昵之间的关系,很现实,也很骇人。可在长久消损下,山上的小卖部畅想,火车上的戏弄,餐馆里的相约,楼台上的烟,阳台上的灰,甚至那个看电视时意识的回身,都是自由的暖光。在日常里,渗入一点似是局外人又似是镜中人的佐料,再添些时空交叠的恍然,还拿各种口号来映照,挺见导演的想法与潜力,但要是拍得、演得、剪得再顺畅些就好啦,毕竟已是个能去“苛求”的好作者了。期待更多岭南叙事。对了,三个男人四次小便,都没洗手……@虞社。三星半,下次加油。
No. 一部非常不好听的电影,也就是说,没有画外的电影,意味着长镜头中的摇镜只能像拖着一团赘肉一样拖着那佯装自然主义的陈词滥调。但你说共鸣?集体记忆?当然有,但这也是我失望的起始点,因为有了共鸣,有了类似的经验,那也就意味着一切只能安安稳稳地抵达终点,别的什么也没有,即便有了第三段那些似梦的场景,但也仅是在梦的视界旁边旋转,并没有真的要入梦的意思。为什么无法入梦?因为不存在逃逸的欲望,没有像片中那个离家的奶奶一样一去不复返的决心(她再也没出现),自然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出格举动,看来理想二字确实已经从华语电影的字典里彻底消失了,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过。
听小伟英语口音,他是怎么被加州大学录取的?
7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厉害啊,处女作能这个程度,很不错了。这片首先好在剧作,非常工整,用心的细节也有很多,剧情的构建,关系的推进也都很合理。相较而言,更喜欢前两部分,第三部分开始玩了些虚的,反而有点无趣了。
有点反感这片,但处女作有这样的掌控力勉强也可以给个及格分。母亲的段落极为功能化,父亲的段落太过超现实,只有自己那段还算有点落到实处。如此一来,字幕卡强行分割的三段本身就仅仅是花招而已,并没有产生表意上的联系,况且视角也并不严谨:儿子的段落中有一个妈妈背着他在门外打电话的镜头、父亲的段落中也有儿子自己闲逛。新导演搞创作,该弃的不弃已经是通病了,充满着算计感。最后,很多国产新导演拍片都有的表演问题,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死气沉沉的表演,重人物的片子连个近景都不怎么推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一到对话戏就是大长全景往那一摆,逢看必睡。
不多见的墙内粤语电影,演员都挺棒。非常私人的家庭故事,也拍出了两代人的一些共通境遇,《一鸣》也贡献了最为自然舒适的校园青春戏。另外荒凉村落已然变成新导演超现实想象集中营,这部分如果延续原本的写实主义或许会更好。
3.5 “惊人首作”名副其实,尽管缺陷不少,导演想做的想要的太多,结构也很有问题,不过这些都掩盖不了导演的才华。
自然流畅,平实生动,跟拍恰到好处,声音处理饱满,处女作就这么沉稳,难得,更喜欢原名《慕伶,一鸣,伟明》,以三个名字命名,以三个名字进行分段。
导演拥有极为细致缜密的理性思维,在景别构图的平衡、剪辑的精确度、视点的转换节点和运动镜头的速率停顿上都下了大功夫。但此类以极端情境反逼人物状态的电影,文本的咬合一定要足够紧,才能制造出具有强烈代入感的戏剧漩涡。遗憾本片依然存在不少泄气的段落,在情感层层推升的过程中制造出不少阻力,所以直到结尾我们也没能真正看到脱离出事件之外的人物,不论是慕伶、伟明还是一鸣,都差了一口气。Ps:旅馆大风停电那场戏蛮惊艳的。
现如今已经很少有处女作能让人一身鸡皮疙瘩的惊艳了,这部作品做到了。导演太厉害了,心思温柔又细腻,个性叛逆又沉默,他看见了父母,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老屋,看见了广州这个城市,像每一个经历过高三与家庭伤痛的我们每一个人,静水流深的情感默默汇入到心底,像给我注入了一剂回忆药水,瞬间把我拉扯到自己窘迫、压抑又自由憧憬的青春时光。黑暗的影院里我这个成年人的眼眶悄无声息地湿了,灯亮起前又悄无声息地擦干,感谢这110分钟的私人自我窥视时间,非常妙非常治愈。
享受这种苦中作乐的幸福感。大陆电影,全程粤语对白,三主演全部来自香港,加分加分!